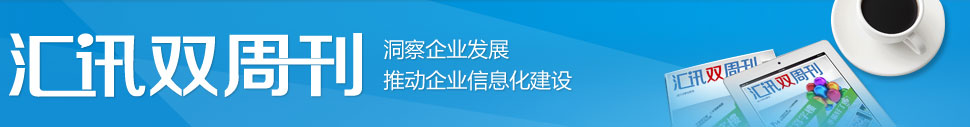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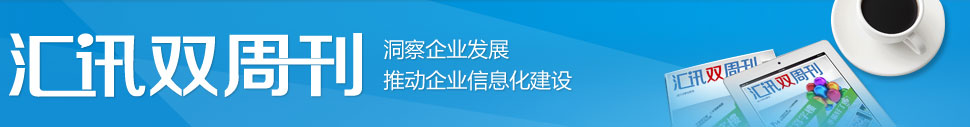
2011-03-14
那天和一個朋友吃飯,他說現在人到了四十,覺得活得特別踏實.面對一屋子的人,再也不用在意別人怎么看自己,再也不用為贏得誰的好感費心思,再也不用為某個剛認識的漂亮女孩的一句話琢磨上半天.
最近我發現,周圍有好幾個以前不說天天歌舞升平至少也是每個周末都要錢柜唐會的四十歲左右的"老男人"陸續收山,工作之外開始踏踏實實地享受家庭生活.他們的生活狀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人更"沉"了也更"靜"了,隨之,他們做事情也變得比以前從容和靠譜了不少.
由此-(對不起我也承認這么寫有點"裝",您先摟著點別吐!)-我居然聯想到了我們今天的社會.
不過,我還真是覺得,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走到今天,特別是在這場殃及全球的金融風暴之后,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也需要像四十歲的老男人一樣,"沉-靜"下來.
我以前曾經說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從貧窮起步,然后經歷長達三十年的平均接近雙位數的GDP增長,社會不浮躁、價值觀不錯位、貧富差距不拉大,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線提升,我們這個社會就像是一個情竇初開、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看見個女蝴蝶都能想入非非的毛糙小伙子.我們睜開眼睛,好像滿世界都是機會,到處都彌漫著誘人的人民幣味道.
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在生意場上看到的所謂"成功"往往都是空手套白狼,小驢拉大車,拆東墻補西墻,左兜裝右兜;是把短貸當長貸,把貸款當投資,把投資人當弱智,把創業當畫餅,把上市當圈錢,把盲目投資當多元化經營,把價格戰當企業戰略,直至把忽悠當營銷,把詐騙當資本運作,把神經病當企業家;是比誰能讓自己集團公司下面的結構圖復雜得讓自己都看不明白,是比誰能用最少的代價博取最高的回報,甚至是比誰的膽更大、心更黑、手更狠、人格更分裂、大腦更潮濕.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各行各業都在急不可待地尋求短期回報,掙不該掙的錢.做房地產的靠賣戶型圖掙錢,開醫院靠賣藥掙錢,做市場營銷的靠廣告回扣掙錢,做媒體的靠發軟廣告或扣發負面新聞掙錢,做零售的靠廠商返點掙錢,軟件殺毒的靠投毒掙錢,券商靠通道掙錢,送貨的靠賣客戶名單掙錢.而且心情一個比一個急切-大學畢業三年沒買車買房感覺像是失敗者,創業三年沒上市就開始灰頭土臉,別人通過研發做出什么好東西我必須在第一時間"山寨",拍個電視劇為了能賣座哪怕杜撰個車禍也得炒作,藝人二十歲還沒紅恨不得集體找個地方撓墻然后跳河.
與此同時,我們的內心卻越來越脆弱,越來越焦灼;我們的精神家園越來越荒蕪;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越來越深地迷失在GDP陡峭上升的曲線中.我們的媒體經常分不清什么值得推崇與羨慕、什么應該質疑與警醒;我們有時甚至分不清什么應該尊重、什么應該鄙棄,分不清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什么是好什么是歹.
我們的網絡成了垃圾場,很多人不是在那里享受理性而有尊嚴的言論自由,而是毫無顧忌與遮擋地享受著當眾排泄的快感.形形色色以排外、仇富和國際陰謀論為主要訴求點的狹隘民粹主義、經濟沙文主義和流氓無產主義的聲音讓我們這個動不動就要抵制這個抵制那個的社會有時候乍看上去就和一群十八、九歲的憤青喝了大酒一樣.(前一段有本書叫《中國不高興》-這種商業化包裝下的偽憤怒和芙蓉姐姐或者腦白金一樣,出來溜達是人家的自由,有人買帳一定是我們自己閑的.)
所以我想,中國經濟走到今天,現在也許是我們真正開始長大的時候了.我們要從浮躁沖動、狂放不羈的毛頭小伙子變成淡定沉靜、擁有更多理性與責任感、懷抱更多誠意與善良的"四十歲老男人"的時候了.譬如-
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國際社會上應該塑造更加理性、沉穩、能當大事的形象?
我們的政策法規是不是應該具有更多的明確性、可操作性、長期性與一致性,而不是"留的空比填的空多"一切為了解讀方便?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應該投入更多到教育、醫療和環保,而不僅僅是基礎設施與全球制造?
我們的企業是不是應該投入更多到研發與企業文化,而不是僅僅是渠道與營銷?
我們的國企是不是應該沉下心來解決一些同機制和文化有關的深層次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加主動而自覺地維護版權與知識產權,而不是鼓勵和縱容盜版和山寨?
我們是不是應該鼓勵更多的創業者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從"三年上市"、"五年過億"變成"三、五十年做成一件能夠影響和改變世界、對社會和他人有益、讓自己驕傲一生的牛事"?
我們是不是應該幫助我們的證券市場從少數莊家的天堂變成理性投資者的棲息地?
我們是不是應該通過引導與監察讓我們在網絡上的聲音變得更加理性、多元、善意和包容,而不是更加污穢不堪和肆無忌憚?
愿我們這個國家能夠在三十改革開放年的一路狂奔之后逐漸沉靜與平和下來,敢于直面深層的問題,而不是陶醉和湮沒在表面繁榮(或者風暴后恢復繁榮)的浮華之中.唯如此,我們才能迎來在國際舞臺上更加強勁而超凡的跨越.